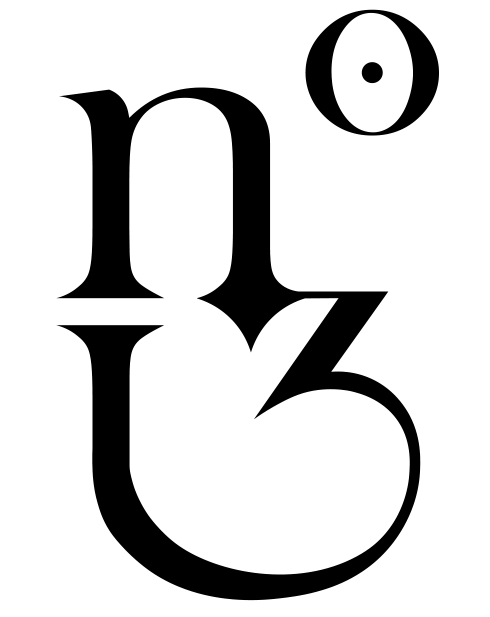自译《辛吉革命》鹿特丹电影节评论
文: Clarence Tsui
译:Nathan Zhe
Link: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reviews/zanj-revolution-thwara-zanj-rotterdam-680323/
在塔里克·特琪亚 (Tariq Teguia) 的第三部作品中,一名阿尔及利亚记者和一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贝鲁特相遇,他们分头行动,四处探访并了解中东地区的人民起义历史。
在塔里克·特琪亚第三部影片的中间部分,一位黎巴嫩历史学家告诉影片的主角Ibn Battuta(由Fethi Ghares饰演):“过去的叛乱可以为今天的思想家提供很多教导”。这句话定义了《辛吉革命》,一部通过寥寥无几的暴动景象掩饰其片名的作品。这部电影与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现居希腊的电影人的前两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作品:2006年的首作《罗马不是你》和2008年的第二作《内陆》一致,这部最新的,主要以贝鲁特为背景的作品以思想冲突取代了武装冲突,因为深思熟虑的探讨和不时的激烈辩论都预示着反抗体制是可能的。
这些关于中东历史和政治的“课程”透露出某种紧迫感,而这种感觉在特琪亚过去那些令人倍感无聊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也许导演受到了过去三年该地区活跃的政治变化的启发并试图以本片进行反映,《辛吉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反独裁政治运动的起伏提供了彻底并具有时效性的知识论述。本片在罗马进行了全球首映(在CinemaXXI的侧边栏中),随后在贝尔福获得了电影节大奖并在鹿特丹亮相,本片将于下个月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墨西哥城的Ficunam)放映。这部电影把艺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显然是对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空间游戏和让-吕克·戈达尔的银幕论战的致敬——并将在独立影展,私人艺术馆和校园中成为常客之一。
影片以Ibn的象征性出场开始,这位记者——与14世纪一位写下大量旅行经历的摩洛哥探险家同名——穿过一片烟雾并在观众的视野中现身。有趣的是,Ghares所饰演的角色已经在特琪亚的上一部电影中出现过:虽然没有名字,但这个留着平头的煽动者在《内陆》的一个短镜头中露脸,他在荒漠上大步流星,兴高采烈地对一个朋友讲述行走如何使自己找回某种人性。
但那是五年前充满政治动荡的时候。现在,Ghares/Ibn看起来明显感到厌倦,并对他工作的意义感到困惑。当他走进一个处于社会剧烈动荡中的阿尔及利亚小镇时,他听到一个戴着面具、投掷石块的示威者提到了赞吉,一位备受压迫,在9世纪的伊拉克反抗其统治者的底层人民。厌倦了 "被要求派往地狱般的地方报道暴乱"的生活,Ibn说服了他的编辑,让他前去为中东人民起义史上这段鲜有人知的事件进行研究;虽然没有预算前往巴格达,但他设法被批准前往贝鲁特,一座被他的上司形容为“记载着阿拉伯民族的惨痛失败”的城市。
上司眼中的糟糕情况被反映在另一条故事线中,即学生激进主义分子Nahla(Diyana Sabri饰演)的家族根源,她和她流亡的巴勒斯坦父母住在塞萨洛尼基(特琪亚本人所在的地方)。她深知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的痛苦——她的父亲,一位城市研究学教授,会说起因为自己的离开而被视为 "叛徒"的痛苦,而她的母亲,一位前武装分子则会感叹她的旧生活永远 "消失"了——这位年轻女子决定通过返回贝鲁特来探索她的根源。她的借口是给夏蒂拉难民营带去一笔捐款,1982年9月,在旷日持久的黎巴嫩内战中,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
在某种机缘巧合下,两位主角在贝鲁特脚手架林立、正在重建中的市中心徘徊时相遇了,Ibn向Nahla询问大学的位置,他要在那里会见一位研究赞吉叛乱的学者。在一次恶作剧般的交谈后,他们发现彼此是迷失在陌生土地上的同类——无政府主义者Nahla嘲笑被问及如何前往 "美国大学"的荒谬——他们将再次相遇。与他们无精打采的本地朋友Rami(Wassim Mohamed Ajawi饰演)一起,他们成为了某种政治化版本的“祖与占”三人组,因为他们谈论激进主义,在摇滚乐中跳舞,并(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抢劫,以确保Ibn和Nahla可以到达他们命中注定的旅程的最后一站——到神话中赞吉的土地和它在巴勒斯坦的现代化身,然后回到混乱的希腊街头。
Ibn完成这一广阔旅程的决心充分说明了特琪亚的野心,因为他为大众媒体每天(若不是每小时)放送的滚动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考虑周到的替代方案。Nasser Medjkane和Hacene Ait Kaci的数字摄影在取景方面做到了一丝不苟,因为角色——特别是Ibn和Nahla——被安置在令人生畏的、非人化的景观中,以强调他们在历史、政治和经济流动中的地位。同时,特写镜头纷纷给到了在Ibn和Nahla的旅程中出现的不知名的抵抗者,包括戴着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农村抗议者、忧郁的贝鲁特难民、抬着烈士棺材的,沮丧的轿夫,以及在影片最后向Ibn表露身份的,疑似赞吉子孙的一位角色。
这种创作理念与Rodolphe Molla的剪辑相辅相成。电影没有采用机关枪式的蒙太奇促使观众分泌肾上腺素,而是让角色在迷茫中根据他们的顿悟所得不断前行,并以此渲染紧张感。
特琪亚这些有趣的,以简驭繁的空间实验反而让影片的缺点颇具讽刺意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用一些不必要的反派人物来填充故事。电影中的反派不出意外的是两位不道德的美国人(由John W. Peake和Sean Gullett饰演),这两位趁火打劫的企业家在伊拉克首次出现;到达贝鲁特后,他们带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装满崭新美元的手提箱住在Ibn住处对面的酒店房间,这个手提箱经常被留在房间内无人看管。
他们的存在可能是有用处的,以便为主角们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来推进剧情,但美国人实在是太滑稽了:他们只是作为代表现代革命者应该反对的价值观的符号而存在,并发表一些将伊拉克重塑为 "资本主义乌托邦"和他们作为 "真正的革命者"进行 "创造性质的破坏"的宣言。这些论述对整部影片的论点没有任何补充;与其试图发掘 "失落的幽灵",也许现在是时候该避免陈词滥调,进行创新和鼓励了。抛开这种强加的,脸谱化的反派,《辛吉革命》传递了一些有价值的想法,供观众在思考反抗制度的意义和可能性时引用。
恶魔的游乐园——自译《电影评论》对阿尔伯特·塞拉的专访节选
文:Manu Yáñez Murillo
译:Nathan Zhe
原文发表于《电影评论》Film Comment 2020年一二月合刊。本文只翻译原刊中出现的采访内容,完整英文采访详见Film Comment官网。
Link: 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interview-albert-serra-la-liberte/
在阿尔伯特·塞拉(Albert Serra)完全虚构的影片《自由》(Liberté , 2019)中,一场变幻莫测,令人不安的性爱游戏正在18世纪的一处“肉体猎场”中悄然上演。
在这部对性欲进行大胆探索的影片摘得第七十二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审团特别奖后,我来到塞拉在巴塞罗那的制片公司Andergraun Film总部并对他本人进行了采访。
电影评论:《自由》展现了一种“自我放纵”式的性快感,你曾提到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的作品对此产生了很大影响。
阿尔伯特·塞拉:是的,她(凯瑟琳·米勒)描绘的不仅是一种肉体的放纵,更是一种对道德的放逐。重要的是去思考这种被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视为“无用”且“偏离于任何形式的社会或固有价值”的放纵需要人们付出什么代价。电影(《自由》)中的一个角色如此说道:“这就是我们为改变世界所付出的代价。” 正因为此,这些渴望极端性体验的性瘾者们才被迫从路易十六(Louis XVI)清教徒式的王室中流亡,最终在不见天日的肮脏生活中栖身。
但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政治代价,我认为其背后反映的对存在价值和审美观的遗弃才更值得一谈。一旦你宣布放弃了你的主观性,独立性,你渴望的和你应得到的——我现在所说的不只是我电影中的人物,更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那么你将要面临的就是人性的毁灭。这便是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作品传递给人的思想。在对性虐待的描绘中,萨德和凯瑟琳·米勒的文字中都包含着一些不易被察觉的微妙之处。如果你决定投入这座性爱乌托邦的怀抱——一处肉体之海摧毁资本主义供需法则的危险之地——那么在那里等待你的将会是一次由人向兽的蜕化。在这个层面上,《自由》唤起的是一种黑暗,残酷且冰冷的绝望。
《电影评论》:在《自由》中出演的人们都来自各不相同的背景,是这样吗?
阿尔伯特·塞拉:没错,虽然我们聘请了一些职业演员,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巴尼奥莱斯(Banyoles,位于加泰罗尼亚东北部,赛拉的出生地)的朋友参演。其中还有一部分我们通过Facebook联系的业余演员,一部分从未出演过电影的戏剧演员。当然还有剧组的人,他们参演了那些尺度最大的情节。例如出演最激烈的S&M鞭策情节的女人原本是布景师,还有一位制作组的工作人员扮演了一个困在三四位性瘾者中间的裸男。
《电影评论》: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你在凭借这部作品对现代压抑的社会氛围做出回应。
阿尔伯特·塞拉:没错,在某种程度上,电影将性欲展现为一种民主力量。在影片呈现的感官与性欲的交织地带中,社会地位与其制造的芥蒂都被无尽的快感化为乌有:支配者可以轻易地转变为服从者,反之亦然。无论你性别,样貌,年龄或财力如何,性爱的游戏向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同时这种追求民主的手段也引发了快感与痛苦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这也是在1970s电影中更为常见的主题。我认为心理和道德层面的冲突才是贯彻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根本矛盾。
近年来,我一直坚信只有虚构之物才能触发真实的共鸣。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只交换了一些表面上的理性想法。但虚构作品可以让我颠覆你的想象并让你的想法变得更加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许会失败,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说到底这只是部电影而已。